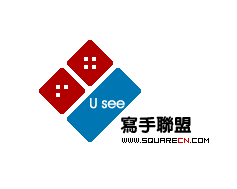碎片
2004-05-22 18:15 | 碎玉
如果可能的话,我宁愿那一天不曾存在过,
重新择路的话,我绝对不会走那条路。
事实上,我不愿看到的都看到了,再“如果”还是看到了。
这几天的风大的邪门,似乎到处都是沙子,从空荡荡的一处跑到另一处。
或许是很平静的。
一个我所不认识的,三十多岁的老男人,
不知在何处询问了一些关于我的事,留了张字条夹到我书里,
美其名曰:同情你的人!
这叫我愤怒,就像是规规矩矩地走在雨后的街上,
却突然被一辆急驰而来的车澎了一身水一样,一股火从心底腾地窜了上来,
被人羞辱了的感觉,凭什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,
以你自以为完整的形体大言不惭的来对我说“同情你!”
是我心态不平衡,可是我为什么要平衡心态,
在人告诉你“同情你”之后平静地说“哦,我接受你的同情”
我做不到!也不想做到!
曾经答应过,不再拿此说事,闷声不语地撕掉这张纸,
实在不想再看到有人对我说“我如何如何帮你。条件是你嫁给我。”
我没那么下贱。
木呆呆地坐了一上午,起身离开了座位。
这昏昏愕愕的一天,到底要多少人要倒霉?
一辆车过去了,然后就有一个人躺在了车下,
只那么一会儿,他便穿了由他血染成的红衣服,
我一向惧怕没有生命气息的东西,这让我更恐惧,更害怕死。
他睁着眼,他的眼睛在看什么,那么无力,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么?
他很痛苦,是不是?
他的嘴巴张着,他想说些什么,他想说他不想死,是不是?
突然间,一股寒意从脊背上爬上来,我机伶伶地打了个寒颤
我不想看见啊,真的不想看见
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居然和鸡雏一样,我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。
我想逃掉,快快地离开这儿,我害怕啊,可是我怎么也走不动。
救护车的声音真刺耳,白大褂把他和他的内脏一同拿到担架上的时候,
我忍不住干呕起来
这是个人啊,可是却如此支离破碎了,
我不想看见,生活那么美好,我才十九岁啊,我不想看到这些啊。
一个人就这么消失了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恐惧这没有生命气息的东西?我不知道
突然很想抓把针来反复穿戳着自己的身躯,迷蒙的警醒敲打着,
所谓这些无辜,善良,你不觉虚伪吗?你不为这虚伪脸红吗?真该拿针戳醒你,无耻的东西,卑下的乞求些什么?所谓的你在乎吗?小心翼翼地维护些什么?
无耻的东西!
一连串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心里转了两圈,消失了,这一滴滴渗出的血珠暖暖地存在着,我感到自己的存在了。一种痛。
那样一滩血,那样一个人,就那么摊在我脑子里,我不想看见,我真的不想看见。
人,有所知才会有所怕,有所见才会有所怕,我宁愿我不见、我不知也不想怕。
我不想怕,救我!
通常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,都会积起很大很大的心理障碍。
自相矛盾的话语,我知道不该怀疑些什么,
我在怀疑什么?我还是不相信自己?
我不知道,我真的不知道,你不要问我。
她说“姐姐,母亲,情人”
他说“那么进黑名单吧”
心模模糊糊的痛着,是伤心?还有心可伤吗?
我张了张嘴,眼泪滑了下来。
楠说:“我烦,我想喝酒”
“是因为你和彬的事情不能够对家里人讲吗?”
她沉默一下,点了点头。
旁边的彬伸过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,那只手里有无尽的爱,
无尽的疼惜--
我想她已经不需要我的安慰了,于是我悄悄地走开了。
夜里的花园比平常要安静些,似乎连空气都是比平常洁净的,
背灯而坐相互依偎的并不一定都是情侣,可是看到这些,
突然间明白即使和人如此,我还是形单影只。
又想起了周,在钻到被子里闭紧了嘴巴悄悄地哭了。
或许只有这么哭过的人才能体会到这“悄悄哭”的份量。
我以为我忘了,将这个不知面容、不知所踪、不知一切的影子忘掉了,
我真的以为--
他所留下的痕迹早已经远了,淡了,再也感觉不到了。
那灰色的影子,从他决定要走就没有再亮过的影子依然微微笑地看着我。
却再也不会看到他了。
记得很清的一次,一个二十三岁女子,痛苦地撑了三天,人们议论纷纷,
我告诉他,我害怕。
他跟我说,那跟你没关系。
他从来不会说什么体贴的话,所以我一直在体会这冷冷淡淡的话里包含着的诸多内容
然而他却留了一帖忏悔离开了。
原来,只是我自作多情。
这是个影子,他在哪儿?他倒底是谁?
这是压在心底的幻觉,这是个消失在网络空气中的影子,我不该。
十九年了,在他之前,和他走之后有一种爱再也没有复醒过。
即使我再爱。
我以为我忘了,是真的以为。
淡淡的紫色,淡淡的蓝色,淡淡的忧伤,淡淡的悲哀。
可能再也看不到他在我面前呈现这些了。
或许真的是到最后了。
-
她没有焰火炫丽
也不像鸟儿会迁徒
不过是放飞的飞筝,
怕你心痛才自由
记忆的线索在你手中
如果你能让她降落
天空如自由,无尽头
可知那颗心在风中太落莫
就让她停留在你怀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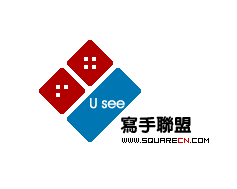
重新择路的话,我绝对不会走那条路。
事实上,我不愿看到的都看到了,再“如果”还是看到了。
这几天的风大的邪门,似乎到处都是沙子,从空荡荡的一处跑到另一处。
或许是很平静的。
一个我所不认识的,三十多岁的老男人,
不知在何处询问了一些关于我的事,留了张字条夹到我书里,
美其名曰:同情你的人!
这叫我愤怒,就像是规规矩矩地走在雨后的街上,
却突然被一辆急驰而来的车澎了一身水一样,一股火从心底腾地窜了上来,
被人羞辱了的感觉,凭什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,
以你自以为完整的形体大言不惭的来对我说“同情你!”
是我心态不平衡,可是我为什么要平衡心态,
在人告诉你“同情你”之后平静地说“哦,我接受你的同情”
我做不到!也不想做到!
曾经答应过,不再拿此说事,闷声不语地撕掉这张纸,
实在不想再看到有人对我说“我如何如何帮你。条件是你嫁给我。”
我没那么下贱。
木呆呆地坐了一上午,起身离开了座位。
这昏昏愕愕的一天,到底要多少人要倒霉?
一辆车过去了,然后就有一个人躺在了车下,
只那么一会儿,他便穿了由他血染成的红衣服,
我一向惧怕没有生命气息的东西,这让我更恐惧,更害怕死。
他睁着眼,他的眼睛在看什么,那么无力,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么?
他很痛苦,是不是?
他的嘴巴张着,他想说些什么,他想说他不想死,是不是?
突然间,一股寒意从脊背上爬上来,我机伶伶地打了个寒颤
我不想看见啊,真的不想看见
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居然和鸡雏一样,我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。
我想逃掉,快快地离开这儿,我害怕啊,可是我怎么也走不动。
救护车的声音真刺耳,白大褂把他和他的内脏一同拿到担架上的时候,
我忍不住干呕起来
这是个人啊,可是却如此支离破碎了,
我不想看见,生活那么美好,我才十九岁啊,我不想看到这些啊。
一个人就这么消失了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恐惧这没有生命气息的东西?我不知道
突然很想抓把针来反复穿戳着自己的身躯,迷蒙的警醒敲打着,
所谓这些无辜,善良,你不觉虚伪吗?你不为这虚伪脸红吗?真该拿针戳醒你,无耻的东西,卑下的乞求些什么?所谓的你在乎吗?小心翼翼地维护些什么?
无耻的东西!
一连串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心里转了两圈,消失了,这一滴滴渗出的血珠暖暖地存在着,我感到自己的存在了。一种痛。
那样一滩血,那样一个人,就那么摊在我脑子里,我不想看见,我真的不想看见。
人,有所知才会有所怕,有所见才会有所怕,我宁愿我不见、我不知也不想怕。
我不想怕,救我!
通常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,都会积起很大很大的心理障碍。
自相矛盾的话语,我知道不该怀疑些什么,
我在怀疑什么?我还是不相信自己?
我不知道,我真的不知道,你不要问我。
她说“姐姐,母亲,情人”
他说“那么进黑名单吧”
心模模糊糊的痛着,是伤心?还有心可伤吗?
我张了张嘴,眼泪滑了下来。
楠说:“我烦,我想喝酒”
“是因为你和彬的事情不能够对家里人讲吗?”
她沉默一下,点了点头。
旁边的彬伸过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,那只手里有无尽的爱,
无尽的疼惜--
我想她已经不需要我的安慰了,于是我悄悄地走开了。
夜里的花园比平常要安静些,似乎连空气都是比平常洁净的,
背灯而坐相互依偎的并不一定都是情侣,可是看到这些,
突然间明白即使和人如此,我还是形单影只。
又想起了周,在钻到被子里闭紧了嘴巴悄悄地哭了。
或许只有这么哭过的人才能体会到这“悄悄哭”的份量。
我以为我忘了,将这个不知面容、不知所踪、不知一切的影子忘掉了,
我真的以为--
他所留下的痕迹早已经远了,淡了,再也感觉不到了。
那灰色的影子,从他决定要走就没有再亮过的影子依然微微笑地看着我。
却再也不会看到他了。
记得很清的一次,一个二十三岁女子,痛苦地撑了三天,人们议论纷纷,
我告诉他,我害怕。
他跟我说,那跟你没关系。
他从来不会说什么体贴的话,所以我一直在体会这冷冷淡淡的话里包含着的诸多内容
然而他却留了一帖忏悔离开了。
原来,只是我自作多情。
这是个影子,他在哪儿?他倒底是谁?
这是压在心底的幻觉,这是个消失在网络空气中的影子,我不该。
十九年了,在他之前,和他走之后有一种爱再也没有复醒过。
即使我再爱。
我以为我忘了,是真的以为。
淡淡的紫色,淡淡的蓝色,淡淡的忧伤,淡淡的悲哀。
可能再也看不到他在我面前呈现这些了。
或许真的是到最后了。
-
她没有焰火炫丽
也不像鸟儿会迁徒
不过是放飞的飞筝,
怕你心痛才自由
记忆的线索在你手中
如果你能让她降落
天空如自由,无尽头
可知那颗心在风中太落莫
就让她停留在你怀中